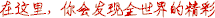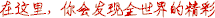聊自己的舞蹈時,侯瑩會提到抽象藝術家羅斯科,“羅斯科的色彩,對我感受力的影響太大了。”而畢加索和波拉克的作品也會被侯瑩拿來指導舞者——肢體背后的情緒,是她對舞者的要求。1月10日晚,侯瑩編導的《涂圖》上演于上海藝海劇院,羅斯科等畫家的名字出現在演出結束后她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的敘述中。
《涂圖》的創作緣起與上述幾位畫家并沒有直接聯系,但“涂”與“圖”,它與繪畫和色彩的關系顯而易見,也讓人自然地聯想到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侯瑩參與編排的現代舞作品《畫卷》。
這一次,舞臺上的六位舞者只是穿著簡約至極的灰色衣衫,在有或沒有音樂的段落,都讓傾訴個人思緒的肢體動作主宰著舞臺。似乎,是沒有任何色彩的“涂”與“圖”。
演出后的觀眾交流環節,被問到《涂圖》的特別含義時,侯瑩解釋了色彩的作用及其從有到無的過程。“最開始這個作品是有顏色的,我希望最后舞臺上呈現的全部是色彩,舞者的身上、地面、四周全部是顏色,而舞者會在地面上書寫“涂圖”兩個字。”但在排演第二個版本的《涂圖》時,“我發現我已經不能再用顏色,顏色對我來說有點太多了。我嘗試用舞者的肢體,在空間、在地面、在能想象和不能想象的整個空間,用身體去構造五彩繽紛,但這色彩不是肉眼能夠看到的,是需要我們去想象的。”
《涂圖》是侯瑩2009年為廣東現代舞周排練的作品。那時她剛從美國回來,想把在美國學習吸收的所有技術,包括莫斯·坎寧漢、特麗莎·布朗等的后現代大師的技術,及沈偉的技術,還有自己的東西整理出來。整理的過程中她發現,對于豐富的身體語言而言,只關注肢體是不夠的,“整合的東西是我要表達的,而動作和身體是技術性的。”侯瑩內心的轉變促使她除去了《涂圖》中的顏色。
不需要呈現色彩的道具,不需要完整的引領舞者和觀眾的音樂,不需要塑造人物形象,不需要故事和敘事。《涂圖》以抽象的動作為載體,舞者表達個人的情緒與內心歷程的過程,也是喚起觀眾的情緒與思考的過程。控制、依賴;親密、冷漠;個人、群體;新生、逝去;人生、宇宙……舞者呈現的動作與場景,需要喚起觀眾投射出自己的情緒與情感去理解。
侯瑩把現代舞的開放與包容傳遞開來,面對自認是外行的觀眾,她說:“請大家不要說不懂舞蹈。任何東西都沒有身體那么有感染力和魅力,如果我們把它做好了。舞蹈無聲,但有更多可能性去意會和感覺。”
在美國時,侯瑩曾是沈偉舞團的一員,她不回避其他舞蹈家對自己的影響。但當有觀眾說在《涂圖》中看到了皮娜·鮑什的舞蹈元素時,侯瑩的回答很明確:我沒有吸收她的動作。“皮娜·鮑什的作品我看過很多,我也非常喜歡她的某些作品,但是實話講,她的肢體對我來說有點太美了,我的舞蹈不會采用那么多特別美和抒情的動作。”
不久前在龍美術館的一次沙龍活動上,侯瑩充滿留戀地回憶自己編導的第一部現代舞作品《夜叉》,在她看來,它從名字到動作,都不美,但因為“單純得完全屬于自己”而得到特別的珍愛。
1993年,具有中國舞、民間舞背景的侯瑩決定改變自己跳舞的方式,加入了廣東實驗現代舞團。聘用她的曹誠淵曾回憶說:“侯瑩在廣東實驗現代舞團中,一直是個傳奇。她于1993年從北京武警文工團轉來廣州,參加剛建立不久的廣東實驗現代舞團,以超強的舞蹈技術吸引目光,卻又特立獨行,曾經一次在所有人都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自己把頭發和眉毛全都剃光。她的編舞能力很早便嶄露頭角,于1996年以自編自演的獨舞作品《夜叉》,在白俄羅斯舉辦的現代舞編舞大賽中摘得金牌。”
“每個人都有一種方式作為表達(觀點)的載體。藝術創作,首先要關心人,也包括自己。”侯瑩追求肢體的美,她尋覓和表達的,始終是自己。對于一位觀眾“不自由在尋找自由”的解讀,侯瑩表示認同,“這就是我們的現狀、社會的現狀、人存在的現狀,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的現狀。”
2006年,侯瑩在紐約成立視野舞蹈劇場。2008年北京奧運會后,她離開沈偉舞團,并決定回國發展。2011年,視野舞蹈劇場更名為侯瑩舞蹈劇場。
通過現代舞,侯瑩挖掘自己、了解自己、思考自己。“在這個過程中,如果說我不關心人,或者說我不關心我的生存狀態,不關心環境,不關心世界發生了什么,內心就不會有觸動。藝術還是來自內心的東西。”平靜的表述像一段獨立宣言,“我最關心我自己,我最關心我自己是怎么想的。我最在乎我自己是怎么思考的,最在乎自己是怎么感受的,最在乎自己內心深處對什么是有感知的。當我開始了解和關注自己的時候,我才能感知這個世界。”
在劇作家、劇場導演張獻看來,侯瑩是“舞蹈界僅有的幾個有當代藝術感覺的人”之一。
她與當代藝術家的合作,則可以追溯到1998年在廣州參與邱志杰的作品。邱志杰在《新媒體藝術的成熟和走向:1997~2001》一文中寫道:“我在廣州新版的《九宮-千字文》中邀請廣東實驗現代舞團的光頭舞女侯瑩在裝置中根據隨機圖像和音樂隨機起舞。”
2001年赴美之前,侯瑩在廣東實驗現代舞團跳了7年,在廣州,她與頗有影響的“大尾象”工作組的林一林、徐坦、陳劭雄、梁據薈等藝術家關系不錯,“去他們的工作室玩,看他們做裝置,做一些互動,非常有感覺。”
2013年,受藝術家譚平作品啟發,侯瑩創作了獨舞作品《燃》。“以其他藝術家的作品作為載體,這是唯一的一次。”對她而言,這是同一種語言的兩種不同表達,“其實不是跨界,超越了媒介,他的筆就是我的心緒,他的語言就是我的舞蹈語言的延續。”1月16日,在北京嘉銘藝術中心的譚平油畫和素描新作展開幕式上,侯瑩將現場表演《燃》。
羅斯科曾否認是抽象畫家,認為自己更注重的是精神的表達。侯瑩說:“我真正感興趣的不是畫和舞蹈,是創作的理念和心境,是過程。是片段性的、沒有結果的、無意識的。心緒都在過程中展現。”
從2009年開始排演的《涂圖》,到2011年的《介》和《介2012》,再到2013年的《燃》,侯瑩創作的同時也重新開始觀察國內的藝術發展。她的結論是:“我們自己的藝術是停滯的,整體性的(停滯)。”她評判的標準是思維的開放性、自由性、多變性。“藝術面臨的危險,與做人有關系。”
面對外界給予的“純粹”的評價,她非常困惑:“我不知道不純粹是什么樣,做藝術還有別的方式嗎?藝術的問題,看大家的生活狀態就可以(看到)。”
對于自己投身藝術的原因,侯瑩的結論是“要用最好的東西竭盡全力地打發時間”,必須也只能用“積極的有創造力的東西去打發時間”。她用來提醒舞者的一句話是,“你的演出可能改變觀眾一生,讓他在一生中有一刻感受到一點點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