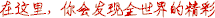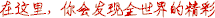舞蹈藝術家,1958年生于云南,洱源白族人,以“孔雀舞”聞名。1994年,獨舞《雀之靈》榮獲中華民族20世紀舞蹈經典作品金獎。2003年,楊麗萍任原生態歌舞《云南映象》總編導及主演。在2012年央視春晚以舞蹈《雀之戀》,再展舞蹈詩人的風姿。
出生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饑餓記憶為她的人生啟幕,“我記得我奶奶都是趁著半夜爬過河去,摘南瓜來給我們煮著吃”;經歷十年“文革”,她骨子里流露著悲觀,“我對人性很悲觀,我很警惕”;四十年舞蹈生涯,她自稱守望之人,“小時候就知道跳舞是生命需要”,“我在這里守候,我是守望的人”。她說,我看到事情的真相,太多利益對我沒意義。她,就是舞者楊麗萍。
我對人性是悲觀的,我崇尚自然現象
問:除了自己個人生活以外,我看您很少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討論,針對一些社會議題您是什么態度
楊麗萍(下稱“楊”):不太想去,但我對人性是悲觀的,因為我們經過“文化大革命”,所以非常警惕,我很警惕,像孔雀一樣警惕,小心,因為人是最可怕的動物,要不杰克遜就不會死了。
問:1971年進入版納歌舞團的時候,正值“文革”。
楊:所以看到很多,看到人吃人,人傷人,現在一樣的。現在隨時人都會傷害你,他們甚至傷害你不知道為什么傷害了你。
問:那個階段會在你身上留下什么樣的政治印記
楊麗萍:不光是“文化大革命”,現在一樣的,只要你給人機會,給他時間、土壤,說現在可以放火了,你看他就會到處放火了,現在沒人管沒法律了,他就開始砸窗戶了,他就開始拿著機槍掃射了,所以我很悲觀,人很復雜。
問:您覺得這種復雜是什么
楊: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樣打開了,什么都出來了,蒼蠅、蚊子、孔雀全都放出來了。
問:這是不是也影響了您對婚姻和歸屬感的理解
楊:我很崇尚自然現象,大企鵝養一個小企鵝,它可以一個月不吃東西,然后把它養大了,小企鵝長大了就走了。企鵝與企鵝之間就是這樣的一個,它們也有集體,它們也有一個個體,這樣的一個自然現象。不太喜歡一些約定俗成的東西,一些規定,約束,我那個《孔雀》里面的第一幕就是鳥籠,我在上面,把它們放走讓它們自由。
跟孔雀學著做人,盡量去奉獻
問:在您的理解中,婚姻只是一種關系,一種契約,憑需要來取舍它的存廢,不必太過糾纏,那人跟人的這種關系是否構成責任
楊:在這個社會上很難,很難跟人相處,就是要以善待人,盡量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然后盡量不要索取,比如說兄弟姐妹,你給予別人的東西,你不要想他要夸獎你,說大家對我很好,這個不需要。
人要找到一個愛的感覺,跟一個人相愛,然后那個人就會要求你,你就要有責任,所以你一般都簡單一點,盡量去奉獻,我的態度就是,基本上就是盡量去奉獻。比如說我要去哪里演出,就按我的想法,我就會說我來演出,他問你需要多少錢,你的演出費多少我說你出個價吧,我不會出價,你愿意出多少,我覺得合適我就去,不合適我就不去,就不會去給別人一個非常大的壓力,你可以選擇不去。
問:您排斥這個嗎
楊:我不是排斥,我看到事情的真相,都是太多利益的,對我來講沒有意義。我喜歡用舞蹈,用藝術,用精神跟人去交流,而不喜歡用一些這種七七八八的東西。
該什么時候開門,什么時候關門,這個度,不能什么都不知道,跟這個社會隔絕,也沒必要。希望我們永遠在原點上,世界再紛亂,再亂,你永遠不去繞圈,你永遠在最原點,你肯定要去慢慢轉,最后還是回到這個地方,出生地就是始發點。
人太復雜,其實我們就是一棵小草
問:談談您的價值觀。
楊:就是特別像自然里的。
問:還是要回歸到自然。
楊:一棵樹長大了,它長起來了,能讓你呼吸到氧氣,然后它給了你綠蔭、清涼,然后它自己是靠著陽光,靠著大氣存活。只要你不去砍它,人為地把它砍壞,它自己就會生長,然后這就是它的價值。但它為什么要長那么大,沒人知道。你去問那棵樹,或者問太陽,你為什么要給我們光明,是我們要給你錢嗎你照亮我們,就這么簡單,這就是太陽的價值觀,月亮的價值觀,包括一棵樹的價值觀。
我們人太復雜,其實我們就是一棵小草,你想宇宙有多大,我們根本就是一個小細胞。我們用光的速度都找不到宇宙的盡頭。然后我們好好在這里,我們一個生命最多一百年就逝去,然后再生長,世紀永遠在更替,從發芽、開花、結果、掉葉子和下雪,然后再發芽,都是在輪回。太短了,人的壽命太短了。所以這么多東西我就不想去想,因為太沒用。我的價值觀是什么不想去把它說清楚,如果要用文字說清楚,就像我怎么去比喻這么一棵樹,或者太陽。
問:您從什么時候有的這種體悟
楊:我就是從自然里學的,就是跟那些僧人學的,跟孔雀學的。我要是有個孩子我也不會強迫孩子做任何事。我現在沒說你必須要上學,你想學這個你就學,我會指導她,跟她談,平等地談,而不是強迫的,然后盡量地給予她,然后在她身上發現她,告訴她,讓她找到自己,這個就是我的方法,這個很簡單。
不是商業而是生存法則,靈魂也要吃飽的
問:外界對您還有一個評價是“在商海摸爬滾打多年的并不天真的藝術家”,商業和藝術,最難兼容的兩個事情,在您這里似乎得到完美的結合
楊:我們是在原點上,我們在始發點,我們也在終點,我從來都在這個點上,所以我是特別清晰地知道。在2000年以后,人們知道一個電影要拍出來一定是要有票房的,2000年以前就是誰愛票房誰不是藝術,你看現在人才明白。我跳《雀之靈》的時候就已經知道,我這個舞蹈出來以后,跳出來以后一定是跟人有關系的,是人需要的,是可以買票來看這個作品。
所以我2003年演的《云南映象》一樣,走到哪都是票房,從舞蹈門類票房上沒有問題,這個是一種生態的平衡。你說我們一群人跳了半天舞蹈,我們花了那么大的體力,我們跳舞是要花體力的,我們跳了那么多,我們感受到了,我們的靈魂有了寄托,然后我們跟人沒有關系,這是欠缺的。就好像太陽出來沒有用一樣,我們太陽出來,太陽升起來一定是它跟我們每一個人,跟我們的宇宙,跟我們的地球是非常的相關。
我們是舞臺藝術,我們不是小時候的,在篝火邊上自娛自樂,我們只要一進到劇場,我們就會是一個儀式,宗教,舞蹈宗教。人是要信宗,有信仰的,觀眾就是信仰,也跟我們一樣信仰,所以他們來看我舞蹈,所以我們都是有信仰的人,就是舞蹈是我們的信仰。
這不是商業,這就是一個食物鏈,是一個生存法則,因為人們不單是要吃飽肚子,靈魂還要吃飽。比如說我們在臺上跳舞,觀眾靈魂沒有吃飽,所以你必須是又要有精神的,又要吃飽肚子,這是個特別簡單的,這不是商業。這叫一個非常和諧,很生態,我們活得很生態。
問:現在有“出書熱”,您本人好像從未出過書,為什么
楊:你要出書,就像跳舞是你擅長的,出書不一定是你(擅長的),出什么,有沒有意義你只是為了出一大堆書,然后不停地送人。